渤海湾里去钓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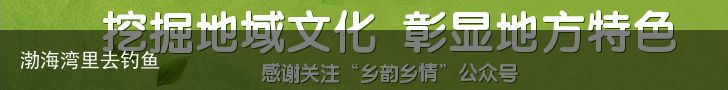
《董乡文学》杂志选稿平台第692期
渤海湾里去钓鱼
作者:窦学斌

金秋十月,秋高气爽。启明星快要下班了,我们钓鱼小分队一行七人已车马劳顿近两个小时赶到了广利港。
“老板,老板,起床了!”只见这次活动的组织者,县城有名的海钓大王——老庞,矮矮的个头,宽宽的肩膀,头上戴了一顶黄色的迷彩长檐单帽,身上背着一个长长的老帆布式的大黄钓具包,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卷,在漆黑的夜幕下,深深地吸了一口,那嘴上的火星一闪一闪的显得格外明亮。左手使劲地拍打着广利港船老板的宿舍大门。我们其他几个队员像游击队员样各自背着自己的“长枪短炮”,在微微的寒风中静静地等待着。
不一会儿,灯亮了,从屋里走出一个手持手电筒的人来,那雪亮的手电光就照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,耀得我们急忙用手臂去遮挡自己的脸。“走,走,抓紧时间上船啦。”那人急火火地用手电筒向前方照出一条明亮的路,带领着我们穿越了宿舍区,来到了广利港码头上。我们放眼望去,只看到夜幕下那广利港上的帆船一艘挨着一艘,一片连着一片,那船楼子和船舱里的灯光闪闪烁烁,星星点点,此景此情使我突然想起了杜甫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诗句,不由得感叹道:广利港好壮观啊!
“走,走,快跟上。”后边的王大哥看我沉浸在夜幕下的美景中,便大声地催促我道。我猛得一抬头看到前边的几个人已越过了船码头,便紧跑几步追上前边的人。“大家注意了,看好翘板,注意脚底下,千万莫踩空,上船了,上船了……”那船老板首先用手电筒照着那长长的翘板爬上了帆船,站在船头上,然后回过头来一边照着翘板一边招呼着。大家顺着陡峭的船板,背着沉重的钓具包,颤颤惊惊地手脚并用地一个一个地爬上了木帆船。“大家各自找好座位,坐稳了,一会儿就开船了。”我们几个人每人都找好了自己的座位坐下来,不一会儿那船也就发出了“突……突……突……”的声音,只见那木帆船在港湾中转了个大圈,径直顺广利河向东驶去……

天上的星星眨着眼晴,好象在和我们对话:“今天你们几个起了个大早,一定会钓到不少的鱼呢。”船慢慢地前进着,两边的河滩上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,只觉得两岸快速地向脑后跑去。我望着东方的天际,看看大家,下意识地向庞大哥近前靠了靠说:“庞大哥,你经常来钓鱼应该有数,你估计今天我们能钓多少斤鱼?”老庞看了看我们,十分自信地说道:“没问题,没问题,五六十斤应该把握吧。”我一听一天能钓五六十斤,高兴极了。赶紧搬着自己的座位又往老庞近前靠了靠,激动地说:“那太好了,钓了这么些年的鱼,还真沒钓过这么多一次呢。”“那也得看今天的运气了。”老庞脸一沉,一本正经地说:“一方面是运气,一方面是技术。”“噢,这里面当然有技术了。”我顺着老庞的语气说着“论技术我们几个可不行了,海钓我们还很生疏,全凭大哥你指教了。”“指教谈不上,但经验还是比你们多嘛,因为我来钓鱼的次数多了去了。”身边的小王插嘴说:“庞大哥来过几次呀?”没等庞大哥开口,他们一块来的老张师傅抢先一步说道:“老庞嘛,是咱县有名的钓鱼大王呢。”哈哈哈……大家一阵哄笑。他们一块来的小高师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:“老庞啊,是个真正的海钓玩家,每周至少海钓两次,来广利港这是最近的。”他们一块来的小张师傅站起来,向我们几个挨了挨,笑着给我们说:“近的去过潍坊港、滨州港,远的去过东营港,辽宁港,全国各地海钓都有老庞的身影呢。”说到这里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这时只见老庞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一支笔香烟,一边分烟一边十分骄傲地说:“说真的,我每年的海钓费都在五万元左右。你们信嘛?”“啊,真的?”大家听了十分惊讶。紧接着老庞用打火机点着烟,并深深地吸了两口,说:“你们那海竿转轮买的是多少钱的?那主线是什么线?”;我们听后吓得没敢吭声,坐在我后边的王大哥急忙说:“我们买的那转轮都是五十多元一个的,那主线都尼龙线的。”我本以为王大哥是个钓鱼迷,购买钓具时舍得花钱,应该算很好的钓具了,殊不知,在老庞那里简直就是残次品。我与小王都是购买的三十元一个的转轮,全部使用的是尼龙线。老庞听了哈哈大笑:“你们真是没玩过海钓,没有经验,这些钓具只能在内陆湖泊里钓鱼使用,真去海上钓鱼那可就不行了,差远了。”王大哥一边说一边从自己的钓具包里拿出一套钓竿,给庞大哥他们看。庞大哥接过王大哥手中的钓竿边摆弄边说:“这轮这线在海上根本不能用,到海上一甩一拉那尼龙线就断了,真的钓上个大鱼来非断线不可。不是跟你们说着玩,那海里时常有大鱼上钩呢,不信你问老张师傅。”这时你再看老张师傅。“就是,上次在东营港就钓上了个大鱼,只看见它那黑呼呼的鱼脊就有大半米长呢,最后挣线跑了。”我们几个听了感到很玄乎。紧接着小高师傅又说:“上次在天津港庞师傅就钓上来了一条二十一斤的大鲈鱼。那次庞师傅可累坏了,和那大鲈鱼搏斗了好长时间,最后幸亏人多,又有一个大抄网,它才没跑掉呢。”听到这里大家感到惊心动魄,越发担心起自己的钓具来。“你们的钓具一是转轮质量差肯定寿命短,二是线没有拉力,在海上一拽就断了,不信海上试试。”老庞不无骄傲地说着。我们三人听了心里一阵阵哇凉,心想:今天没有大财发了。幸亏在来的路上跟着庞师傅去了垦利县城,每人又购买了十套钩架,二十个大铸铁坠子,一兜海蚯蚓,也算是有备无患了。

船不紧不慢地迎着太阳向东驶去。东边的天际像无边的红霞布满了整个天空,红彤彤的太阳慢慢跃出了地平线。大海的早上风平浪静,那一望无际的大海宽阔无边,茫茫的海水浩瀚如镜,那小小的船儿真如海上的一叶扁舟。我们内陆的人平时生活在陆地平原,真得没见过浩浩汤汤的大海,面对无边无际的海水真有些毛骨悚然的样子。我在想:这要是真得掉入海中那可就真得没救了,只有喂鱼的份了。“到了,到了。”船老板一声高喊打破了我的沉思,我猛得一怔,才看到船老板正准备抛猫停船,“这里就是钓场了,请大家先进船舱喝碗热面条暖和暖和,吃了饭就开始钓鱼了。”“交钱啦,交钱啦!”这时老庞右手夹一支香烟急火火地凑到嘴上吸了一口,一边走一边咋呼着。我们同伴中的王大哥放下手里的鱼具,从怀里掏出钱包,“三百元,给。”老庞接过那三百元钱径直去驾驶舱找老板去了。
等我们三人吃了面条走出船舱,已看到老庞他们几个都上了行头。最为耀眼的是老庞了,只见他头上戴了一顶硕大的防风帽子。说是帽子,其实就是防风防晒的大头罩。戴上它会把人的头、耳、脖、肩全部覆盖在头罩里面,那头罩耳边只留了两个小孔,面部只露了俩眼,其他都被厚厚的帆布包裹着,在海上既防晒又防风,像电影里的那些洋鬼子样滑稽可笑。我看到他们个个面前都已支好了二、三根海竿,高高地斜立着像机关枪。我们三人见状,也迅速地各自整理自己的钓具。有的支竿,有的顺线,有的挂饵,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时我只看到邻居老张师傅,架好了甩竿,顺好了主线,然后又把一串五个钩的钩架连接在主线上,又急火火地给五个钩上饵。当饵挂好后又顺了顺线,然后站起身来,两手撑开鱼竿,两脚前后分开成马步,双手架竿,瞅准正前方,用力一甩,那铁坠子就飞出去了四十多米远,只听“嗵”地一声响,那成串的鱼钩就落入了水中。老张师傅又迅速地摇了摇大转轮收紧了渔线,坐下来等着。一会儿又看见老庞、小高、小张师傅纷纷抛竿下钩,那“嗵、嗵、嗵”铁坠落水的声音,足以说明海钓已经拉开了帷幕。
“快,快,上鱼了,上鱼了!”只见老庞像发现了敌情样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,两手奋力一拽那鱼竿,然后快速的旋转那转轮,此时只听到“吱……吱……吱……”转轮发出的声音。这时你再看那老庞嘴里高喊着:“上鱼了,上鱼了,还是条大鱼呢!”兴奋得用两手死死拽住那鱼竿,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拽住那线。可拽了一会儿感觉不对劲,怎么拽也拽不动了,才知道鱼钩挂在了海蛎上了。便十分沮丧地说:“遭了,遭了,钩子挂到海蛎上了!”一边说着一边立起身来在船上不断地调整着角度,千方百计地想摆脱海蛎子,把钩子脱下来,可无论你怎样变换角度,那五个串钩总是死死地咬住海底的海蛎子不放,周旋了几分钟,庞师傅看脱钩无望了,也就狠下心来用上全身的力量把那子线拽断,重新换副钩架再钓。

“快看,上鱼了。”只见老张师傅猛得站起身来,双手抓住鱼竿使上全身的力气猛得一拽鱼竿,然后快速地摇起转轮来,只听那转轮唰唰作响,那水中的钓线嗖嗖地缠绕到转轮上,雪白的两条鲈鱼离开了水面悬挂在鱼竿上。“哇,好大呀,一个就有斤数,两条,两条呀,就是二斤啊!”老张师傅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,一边急急地收着竿,一边炫耀着刚离水的那两条大鱼。”“哎呀,每条足有一斤多呢,张师傅来了个开门红,这下了好了,是个好兆头。”我惊讶地感叹着,高喊着。
“快看,高师傅又上鱼了。”小王忙碌地支着竿子,猛抬头又看到前面的小高站了起来,快速地收着钓线,断定小高又上鱼了,当我们大家都抬起头时,果不其然看到小高高举的鱼竿上像串糖葫芦样吊着四条大鱼,我们都兴奋极了。“哇,有鲈鱼,有狗子鱼,个头还真不小呢。”小船上一阵阵欢呼。不多时庞师傅、小张师傅也都开了张,有的已上了三条,有的已上了五、六条。快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们一块来的三人一条也没有上,没有开张。越不开张我们三人就越着急,越着急越乱了章法。小王干脆不下竿了,站在那里先看他们钓。我心里更是着急,但没有停下垂钓,先是顺线,再连接钩架,尔后是给五个钩子上饵,等五个钩全部上好饵后,就起身,双手架住鱼竿,前后脚分开成马步型,然后搬开开关双手用力让生铁大坠从头顶飞向正前方,这不抛出去有三十多米远,我想这次有戏了。不一会儿看到鱼竿稍头抖动的厉害,我急忙收线,可当子线全部离开水面时却空空如也,一个鱼也没有。正在纳闷。“快,帮忙啊,钩子又被挂住了。”在我身后的小王这已是第三次被海底的海蛎子挂住线了,“气死了,抛下线去就被挂住,这鱼真得不好钓呢。”“莫着急,慢慢来吧。”我一边帮小王拽线,一边宽慰小王说。我们俩个不断地变换着角度,调整着位置,实在脱不了钩,干脆用尽全身力气把子线拽断,重新再换一副钩架另开张。正当我们几个忙忙碌碌地更换钩架、顺线、挂饵之时,又看到后边的小高师傅高喊着:“上鱼了,上鱼了。”一边快速地摇轮收线,当子线离开水面时三条鲈鱼像糖糊芦样被提起。大家更加兴奋了。我一会儿看看邻居怎样挂饵;一会儿看看邻居怎样甩竿。慢慢我发现邻居所挂的诱饵都是每个钩上挂一整条海蚯蚓,而且让海蚯蚓长出钩子一截,让海蚯蚓悬吊在钩子上来回摆动以引鱼上钩;而我却把一条长长的海蚯蚓截为几段分别挂在几个钩子上,缩小了诱鱼的目标,上鱼的几率自然就低了。突然我看到我的鱼竿尖梢猛烈地抖动起来,邻居也突然喊道:“快,上鱼了,上鱼了。”我急忙立起身来,快速地收线,等我把线收完了,把子线拽出水面时却什么也没有,我有点失望了。邻居老张看到我鱼钩空空,惋惜道:“提晚啦,提晚啦。应早提啊。”我默默无语,又紧张地为每个钩上诱饵、顺线、起身、抛竿。当鱼钩甩出去三十多米远时,心想这次甩得可不近啊,可能有戏。一会儿那鱼又咬钩了,我快速地站起身,急火火地收线,结果又空了。我在想:为什么明明看见鱼儿咬钩就是钓不上来呢?经过认真观察,我发现他们都是在发现鱼咬钩的关键时刻,立马起身先用双手抓住鱼竿,使上全身的力气先猛得拽一下鱼钩,把鱼牢牢地刺在鱼钩上,再火速摇轮收线。不一会儿,我发现我的鱼竿梢头又颤抖得厉害,我快速地站起身,两手拽住鱼竿使劲猛得拽一下鱼钩,紧接快速收线,结果等那串钩离开水面,果不其然有两条大狗子鱼被拽了上来。“快看,上鱼了,上鱼了。”我兴奋地高举着串钩上的那两条大鱼,炫耀了很长时间,才把那两条鱼儿摘下钩。
“上鱼了,上鱼了。”老庞又钓了三条;小张又钓了两条。不多时王大哥也开了斋,小王也钓上了三五条。

太阳已经爬升到了我们的头顶上,钓鱼的人们仍不知疲倦地顺线、挂饵、抛线、提钩,沉浸在海钓的快乐兴奋当中。“开饭了,开饭了,吃了饭再钓吧。”船老板一手拿了块毛巾,边擦脸上的汗边咋呼着。“吃饭了,吃饭了。”老庞第一个放下鱼竿咋呼着大家先吃饭。
忙活了半天的人们早已饥肠辘辘了,一听说吃饭跑得比谁都快,不一会儿大家就围满了饭桌。老板不无骄傲地指着长条桌子上的几个菜,不紧不慢地介绍着:“钓友们,今中午的菜全是自产自销产品,全部来自这片海里:一盘咸海鱼,一盘咸海蟹,一盘咸海鸭蛋,一盘虾酱,一盆清炖鲈鱼。请大家吃顿饭略表我的心意。”老庞说:“白酒啤酒不限量,能喝多少算多少,但应少喝为宜,因为海上风大,船颠波得厉害,小心掉入水里。”大家一看菜也比较丰盛,就纷纷端起酒杯,喝酒的喝酒,吃菜的吃菜。不会一儿酒足饭饱了,大家休息的休息,抽烟的抽烟,好不自在。
太阳偏西了,海上起了西北风,那垂钓的人们沉浸在钓鱼的氛围中,那鱼越钓越多,风越刮越大。那小船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。这时你再放眼看去,那小小的帆船就像漂荡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之中的一个小小的树叶。那大海上空旷无垠茫茫水际,大风吹来,那小帆船随着风浪起伏跌宕,一会儿冲上浪尖儿,一会儿跌到峰底,船上的人们有的已开始眩晕,有的已开始呕吐,这时只见老张师傅一手抓住船傍,一手抓住缆绳,全身随着船的起伏晃动来回摆动着,一会儿把头伸出船外,“哗……哗……哗……”吐了起来;一会儿又丢下鱼竿,两手攀着船傍“哇……哇……哇……口吐白味,想吐又吐不出来,难受得两眼的泪水流了下来,“不钓了,不钓了……眩晕得站不住了。”撒手丢下鱼竿,匍匐着爬行到帆船楼子底下挡风处,干脆睡觉休息起来……你再看那庞师傅迎着风浪,站立在船头,任凭大风吹来,防晒防风帽被海风吹得沙沙作响,海浪不时地拍打着帆船,掀起层层浪花溅射到船的甲板上,老庞依然稳如泰山,只见他双手快速地给五个串钩挂饵,当五个钩诱饵全部挂完时,又开始顺线,当线顺好后,又开始调整方向,一切就绪后只见他双手架起钓竿,两脚前后呈马步型,然后双手用力向正前方甩去,随着“嗖”的一声,那主线就飞出去四十多米远。只听“嗵”的一声铁坠落入水中。“快看,上鱼了。”大家一起呼喊起来,只见庞师傅快速地收着线,当子线离开水面的那一瞬间一串五条的满竿鱼悬挂竿上,全船人沸腾了。
夕阳西下,小船慢慢从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中驶出,渐渐靠近了海岸。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一座座高大整齐,昂首天外的风力发电机,它们有雄壮的躯干和飞速旋转的长臂,远远望去好像一排排整齐、雄壮、威武的列兵;那海滩上最为壮观的一片片望不到边的“红披风”,经秋霜的洗礼更加鲜红夺目。它一棵挨一棵,一片连一片,绵延几十里,几百里广袤无边,好像从陆地伸展开来的大红地毯迎接着凯旋归来的英雄们。

图片来自网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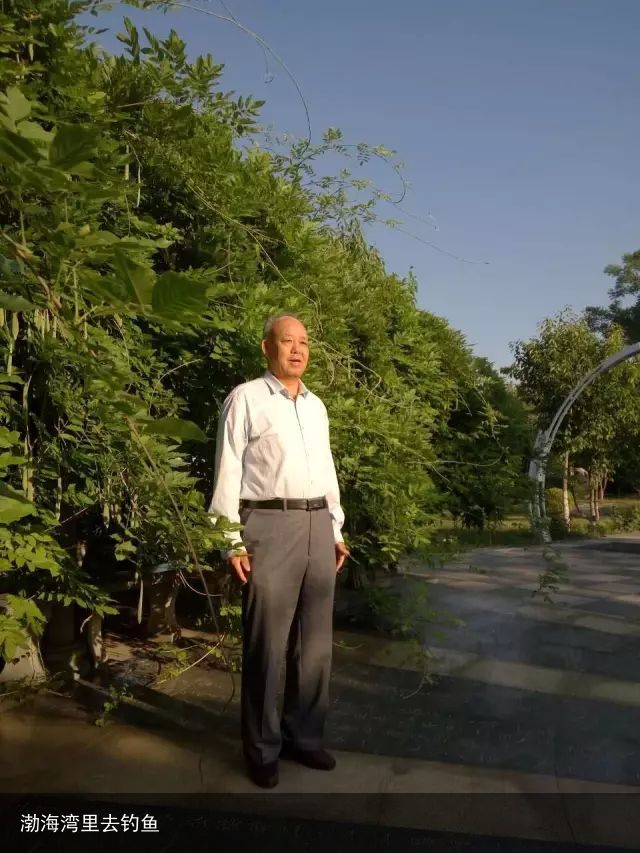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窦学斌,网名:橄榄树。男,1954年2月出生。山东博兴人。字夏亭,笔名古槐秋雨。本科学历。博兴第一中学退休教师。渤海美术书法研究会会员,酷爱绘画、文学。退休后多次参加省、市、县画展,并多次获奖。多篇文章在《今日博兴》和《滨州日报》发表。
窦学斌文集
(二十)我心中的那片净土
(十九)任教安柴高中
(十八)记湖滨农中二三事
(十七)走向新的工作岗位
(十六)报到的那一天
(十五)在那些实习的日子里——见习
(十四)在那些实习的日子里——房东
(十三)丰富多彩的博师生活
(十二)难忘恩师
(十一)步入博师的殿堂
(八)步行卅里去看花裹脑戗裹脑
(六)那飘香的狗肉
(五)在毛主席逝世的那些日子里
(上)
乡情美文——温馨的周末(报刊发表)
征稿启事
《董乡文学》是由中共博兴县委宣传部主管,县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、县文联主办的一份纯文学刊物,滨州市新闻出版局准印。“乡韵乡情”为《董乡文学》选稿平台,希望广大作者踊跃投稿。投稿时请直接粘贴文本,并附有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、作者的照片、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照片请用附件发送。本平台提倡原创首发,原创再发的请注明来源,文责自负。一旦发现违规现象,立即删除,并在三个月内不发表该作者的文章。
董乡文学纸刊主编: 舒中
董乡文学网络主编: 乡韵乡情
责任编辑: 周维东
投稿邮箱
xiangyunxiangqing@163.com
微信:csq456csq

